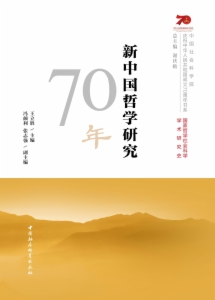第六节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哲学研究
|
来 源
:
|
新中国哲学研究70年 \ -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7 | ||
|
摘 要
:
|
1957年会议召开的背景主要针对当时中国哲学史教学研究中存在着的教条主义倾向,其主要涉及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对历史唯心主义哲学的估价、关于中国哲学的特点和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等问题,其根本问题则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关系问题。其实在冯契此书之前,肖萐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教材中就已经开始用列宁“哲学史是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历史”的理论来编写中国哲学史了。可以看出,尽管冯契、肖萐父等人对于中国哲学史的逻辑发展过程有着不同的认识,但都是在接受了列宁“哲学史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的理论情况下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因此,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势必要突破这个框架,寻找新的角度来认识中国哲学。 | ||||||
|
关键词
:
|
哲学史 马克思主义 日丹诺夫 孔子 哲学 唯心主义 唯物主义 冯友兰 列宁 圆圈 反思 |
||||||
在线阅读
第六节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哲学研究
字体:大中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其不但在政治上指导一切,而且对于学术研究也有着全面指导的“话语权”。当时各个学科的研究都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为指导来进行研究,中国哲学的研究也不例外。但当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存在着简单化、片面化和教条化的倾向,而且受到苏联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影响甚重。因此,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左”的教条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严重地脱离了科学研究的轨道。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了顶峰。“文化大革命”期间,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片面夸大主观意志和阶级斗争,宣扬“上层建筑决定论”,大搞影射史学。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主要表现为把“批孔”与“批林”放在一起,把中国哲学史歪曲、篡改为一部“儒法斗争史”。[※注]
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左”倾教条主义束缚,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思想解放。在中国哲学研究方面,这种思想解放首先表现在对孔子的评价方面。“文化大革命”期间,孔子被同林彪绑定在一起,受到了极大的批判和诬蔑。1978年8月,庞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孔子思想的再评价》一文,最先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中重新认识和评价孔子。在他看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同时代的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不同。因此,不能把一个人物在后世发生的影响和后人对他的利用同一个人物本人的思想混同起来。对于孔子也是如此。批判孔子首先要真正弄清孔子,分辨孔子本来的东西和后世发生的东西,这样才“不致无的放矢,李代桃僵”。他指出:“作为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历史人物,孔子创建了一个学派,提出了一些错误见解,也认识到了一些真理,从而留下了许多为后人由以出发并得以利用的思想材料。后人对孔子思想作过种种解释,并由之发挥出成套的新见解。”对于这些,我们必须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寻找说明,不能不分青红皂白而胡乱加以评价。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认为批判孔子不是完全否定孔子,而是用“扬弃”的办法,批判其错误的、不符合时代发展的内容,继承其合理部分。只有这样,才能否定一切旧的思想和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注]庞朴的这些论述虽然还夹杂着时代烙印,但毕竟从“文化大革命”否定孔子的氛围中迈出了一大步,为后来的孔子和儒学研究奠定了基础。现在看来,这些说法似乎很平常,但在当时却冒着很大的风险。随后,对于孔子的评价基本走出了“文化大革命”中完全否定的立场,大多都从一分为二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和评价。较为重要的文章有李泽厚的《孔子再评价》、金景芳的《关于孔子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严北溟的《要正确评价孔子》等。[※注]如李泽厚从文化—心理结构出发,分析了孔子的“礼”“仁”思想,认为孔子思想已经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这已经是一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存在”。他还指出,历史主义固然不能脱离阶级分析,但阶级分析等并不能取代整个历史主义。在文化继承问题上,阶级性并不是唯一的甚至有时也不是主要的决定因素。只有这样,才能具体分析研究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才能看清每个民族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对于孔子的思想也是如此。只有站在广阔的历史视野和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融会合的前景上才能对孔子有真正的认识。
如果说对于孔子评价只是对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来研究中国哲学反思的一个序曲的话,那么1979年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讨论会”则标志着从方法论上对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来研究中国哲学反思的全面展开。这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山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主办,于1979年10月在太原召开。会上主要讨论了中国哲学史的特点、对象、任务、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如何评价唯心主义、哲学与阶级斗争的关系等问题,其中哲学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点。[※注]这次会议一个重要参照就是1957年1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其讨论的正是哲学史方法论问题。[※注]
1957年会议召开的背景主要针对当时中国哲学史教学研究中存在着的教条主义倾向,其主要涉及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对历史唯心主义哲学的估价、关于中国哲学的特点和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等问题,其根本问题则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关系问题。[※注]而其实质是对以日丹诺夫为代表的苏联学者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史基本问题的反思。日丹诺夫对于哲学史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底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与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末,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注]对于日丹诺夫的这种观点,当时有两派不同的看法:一派对日丹诺夫的观点提出了一定程度的质疑,当时参加会议的大部分学者都持这种看法,在中国哲学史方面以冯友兰、任继愈等人为代表;一派则维护日丹诺夫的观点,以关锋为代表。冯友兰认为,哲学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历史,是哲学史的一般性。其在各时代和各民族哲学史中围绕着不同的问题进行,这是各民族各哲学的特殊性。研究哲学史,应该在特殊中显示一般,这样的一般才是有血有肉的具体真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也必须如此,才能显示它的丰富内容和特点。而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军对垒”的做法,只看到问题的一面,没有看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一面,是有片面性的。因此,冯友兰特别指出唯心主义也有“合理的内核”,“它底合理的部分,应该说是唯物主义的,因为它是与客观事物相符合的”[※注]。按照日丹诺夫的观点研究中国哲学史,任继愈认为会出现三方面的缺点:一是会在社会历史观方面留下空白,使人偏重自然观和认识论;二是忽略辩证法战胜形而上学的斗争;三是没有给唯心主义哲学流派以应有的历史地位。[※注]冯友兰、任继愈的看法虽然不同,但都看到了以日丹诺夫观点来硬套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不足。关锋则与冯友兰等人针锋相对,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敌对的;其界限是分明的,斗争是尖锐的、没有妥协余地的。我们研究它们的相互渗透时必须坚持这个原则,否则就会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注]。
1979年会议讨论的重点也是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其中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对日丹诺夫观点的检讨。在这一点上自觉地回到1957年会议讨论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很多学者对日丹诺夫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日丹诺夫的定义在哲学史研究工作中起到了很多不好的作用,不以原则服从实际,却让实际服从定义,出现了教条主义、公式化、简单化等情况,使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一直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注]因此,这次会议就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重新反思日丹诺夫的观点,即哲学史绝不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那么简单的事情,而是有着锻炼我们理论思维能力的作用。因此,对于唯心主义思想家,不能仅仅判断其思想是唯心论为止,而要“仔细研究他的著作,分析他的论证,才能判断他是在哪一方面失足的。只有这样做,才能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注]。“我们就要为建立科学的‘中国哲学史’提供理论和方法的指导。这个指导思想是什么,就是要完整和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只有从客观历史事实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总结中国过去认识史的发展,特别是哲学思想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规律,但决不能将二者断然对立起来,用以提高我们理论思维的能力。”[※注]
可以看出,不论1957年会议,还是1979年会议,都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固有研究模式的一种反思,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教条化、简单化和形式化的做法。在1979年会议中,很多学者都从马列主义经典中寻找依据,如重视恩格斯“学习哲学是为了锻炼理论思维”的看法、用列宁关于哲学史“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的论述来反对日丹诺夫的观点,等等。其实,当时对于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反思是中国哲学界比较普遍的现象。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时代趋势。在冯友兰、任继愈、冯契、肖萐父等人的著作中,我们都能看到类似的反思。
冯友兰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冯友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但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走了很多弯路:先是向苏联“学术权威”学习,但学到的却是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为条条框框,生搬硬套。后来又按照“评法批儒”的种种说法,致使工作走入歧途。经过这两次折腾,冯友兰自己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反思。在他看来,“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学术上的结论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得来的”[※注]。因此,他要按照自己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来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冯友兰在1980年为此书写的“自序”中说:“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我决定在继续写《新编》的时候,只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不等于依傍马克思主义,更不是抄写马克思主义。”[※注]那么冯友兰所说的“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指的是什么呢?从《新编》的“全书绪论”中可以知道其指的主要是他对列宁关于哲学史的相关理论的理解。因此,他对于哲学史的描述不是日丹诺夫式的而是列宁式的,即“哲学史还有它自己的一般规律,那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些对立面的斗争和转化,以至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不断胜利。但是,在不同民族的哲学史中,在同一民族的哲学史不同阶段中,这个斗争和转化各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必须对于这些丰富的内容和变化多端的形式有充分的认识,才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个规律的意义,更好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方法和原则的正确性”[※注]。除此之外,冯友兰还接受了列宁用辩证法方法研究哲学史的思想,其说:“哲学史是哲学的发展史。它是无限地近似一圈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每一个圆圈都是这一发展的一个环节。”[※注]但在写作上,冯友兰采取的主要还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析模式。从形式上看,尽管冯友兰还没有完全走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但从内容上其却表现出了从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趋势。这种解放首先表现在他对哲学概念的理解上。冯友兰认为,哲学就是人类精神的反思。不但康德的“三大批判”、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如此,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也都分别是人类精神对于认识及政治生活、自然科学研究的反思。在中国哲学史中,每个哲学家的哲学也都是这种人类精神的反思,如孔子的哲学就是他对于古代精神生活的反思。正因如此,冯友兰在《新编》中特别强调中国哲学家对于精神境界的描述,如专门讨论孟子对于人类精神生活的理解和体会、从“越名教而任自然”“心不违乎道”两个层次来论述嵇康的精神境界、对于二程“气象”和“孔颜乐处”的论述以及从人的精神境界来讨论张载的《西铭》,等等。
1979年会议反对日丹诺夫观点的一个主要理论根据就是列宁的“哲学史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与日丹诺夫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观点不同,列宁更强调“认识论和辩证法”,即更加重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统一。冯契就是在接受了列宁的这种哲学史观情况下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他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是20世纪80年代较有代表性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从书名上就可以看出其注重辩证法的特点。在“绪论”的一开始,冯契就表明了他自己的研究方法:“本书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辨证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注]在他看来,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的逻辑发展,才能建立科学的中国哲学史。对于在中国哲学史领域如何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冯契提出了四点要求:把握哲学历史发展的根据、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相结合、运用科学的比较法、站在发展的高级阶段回顾历史。其一个主要看法就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史时,既要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规律,又要注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哲学方面的具体表现。与冯友兰不同,冯契的中国哲学史依据的主要是列宁所说“哲学上的‘圆圈’”理论。在他看来,与黑格尔、列宁所说的西方哲学史近似一串“圆圈”和螺旋式曲线的过程一样,中国哲学史也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也可以比喻为一个由许多小圆圈构成的大圆圈。冯契认为,中国哲学史总体上可以分为两个“圆圈”:第一个“圆圈”开始于原始的阴阳说,经过先秦时期的“天人”“名实”关系问题的争论,最后由荀子做了比较正确、全面的总结,达到了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统一,仿佛回到了起点;第二个“圆圈”则是秦汉以后哲学上关于“有无”“理气”“形神”“心物”等问题的争论,由王夫之做了比较正确、比较全面的总结,在更高阶段达到了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统一。然后各个大“圆圈”又包含若干小“圆圈”,中国哲学史就是在这种看似不断被否定的历史中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其实在冯契此书之前,肖萐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教材中就已经开始用列宁“哲学史是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历史”的理论来编写中国哲学史了。此书是由教育部组织编写的,当时参与的有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等九所院校的老师,后来长期被用作中国哲学史的教学教材。因此,此书在当时无疑有着某种示范作用。此书的一个主导思想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为指导来科学地研究中国哲学史。其所说的马克思哲学史观主要指列宁所说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圆圈”理论。因此,在研究方法上,他们特别强调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在这种理论和方法指导下,他们认为中国哲学史就是“中华民族的哲学智慧在艰苦曲折中发展的合规律的必然历程”[※注]。与冯契不同,他们认为早期稷下道家的“精气说”的宇宙观和“静因之道”的反映论是先秦时期哲学运动的逻辑起点,经过孟子、庄子、公孙龙、惠施等环节,最后由荀子加以批判总结,在更高思维水平上扬弃了孟子、庄子、公孙龙、惠施而向稷下道家“静因之道”复归,逻辑地标志着这一哲学发展“圆圈”的终结。第二阶段哲学发展的“圆圈”则始于张载,中间经过朱熹、王阳明,最后由王夫之通过扬弃朱熹、王阳明而复归到张载,完成了宋明时期哲学矛盾运动的大螺旋。
可以看出,尽管冯契、肖萐父等人对于中国哲学史的逻辑发展过程有着不同的认识,但都是在接受了列宁“哲学史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的理论情况下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这种研究现在看来似乎有些牵强,但却反映了当时学者对于突破日丹诺夫教条主义的某种努力。
任继愈也是在接受了列宁哲学史观点的基础上编写中国哲学史的。在198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的“导言”中,任继愈说:“哲学史是整个认识的历史,这是列宁给哲学史下的定义。同时列宁也指出,在两千年的哲学发展过程中,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柏拉图的和德谟克利特的倾向或路线的斗争不会陈腐。苏联日丹诺夫根据列宁的后一种说法否定了苏联亚历山大洛夫的哲学史定义,其实亚历山大洛夫把哲学史看作是认识史也是根据列宁的说法而来的。哲学史是认识史,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史,这两个说法本来是互相补充、并不排斥的。”[※注]在他看来,无论是日丹诺夫,还是亚历山大洛夫,其观点都是片面的。日丹诺夫只看到哲学史上的两军对垒,没有注意人类认识螺旋上升的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亚历山大洛夫则忽视了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从而把认识的发展看成一种和平的量的渐进过程。因此,只有列宁的观点才是最全面完整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认为哲学史就是哲学发展的历史,其研究对象就是整个人类认识的历史。因此,任继愈特别强调哲学家对于人类认识发展的贡献,“先进的哲学家所以称为先进,就在于他们站在当时人类认识的尖端,给后来人提供了精神财富”[※注]。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教条主义的反思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中较为普遍的现象。这种反思体现了当时中国哲学史研究者在马克思主义固有“话语”体系下认识中国哲学的某些尝试和努力。虽然他们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中国哲学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但毕竟不能超出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个对子”斗争的框架。因此,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势必要突破这个框架,寻找新的角度来认识中国哲学。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