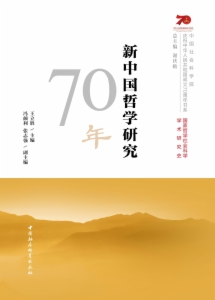第五节 德国古典哲学研究
|
来 源
:
|
新中国哲学研究70年 \ -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13 | ||
|
摘 要
:
|
德国哲学对于中国人似乎有天然的吸引力,中国学人进入西方哲学最早就是通过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等德国哲学家。张世英还把研究重心从黑格尔逻辑学转向了精神哲学,出版了《论黑格尔精神哲学》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强调哲学的中心课题是“人” ,并且用“自由”来概括黑格尔精神哲学的本质。1996年赵林的《黑格尔的宗教哲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和2004年高全喜的《论相互承认的法权— — 〈精神现象学〉研究两篇》 (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出版,使国内黑格尔研究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对宗教哲学和法权哲学、承认理论的重视,表明学界开始意识到黑格尔实践哲学的价值。相信在未来,世界范围内的德国哲学研究领域将听到更多的来自中国的声音。 | ||||||
|
关键词
:
|
黑格尔 哲学 康德哲学 批判 出版 黑格尔哲学 德国 著作 商务印书馆 逻辑学 哲学研究 |
||||||
在线阅读
第五节 德国古典哲学研究
字体:大中小
德国哲学对于中国人似乎有天然的吸引力,中国学人进入西方哲学最早就是通过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等德国哲学家。仅就德国古典哲学而言,“西学东渐”史上,思想文化界和学术界在康德和黑格尔之间的偏重次序至少出现过三次转换,排除早期接受史中的偶然因素,这种偏重多与时代精神的需求相关。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西方哲学整体上被划入资产阶级哲学的阵营,但由于宣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政治要求,更由于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关系,西方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翻译和研究还在进行,尤其是居于西方思辨哲学顶峰的黑格尔哲学甚至一直处于显学地位。改革开放后,中国哲学界抓住了重新审视德国古典哲学的机遇,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焕发了生机,研究的范围扩大,学界对康德哲学的兴趣超出了对黑格尔的兴趣,并且这种热度持续不衰,甚至愈演愈烈。而且在打破了批判德国古典哲学当中的唯心主义倾向的思想桎梏的前提下,同是康德、黑格尔研究,过去比较偏重理论哲学或知识论问题,现在则更关注其实践哲学或政治哲学。第三次转换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至费希特和谢林,其著作的翻译和研究均已初具规模,改变了过去对西方思辨哲学的巅峰时期的笼统认识,向更全面、更深入的方向发展。下文的叙述顺序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学界对德国古典哲学家的依次重视程度而进行。
一 黑格尔研究
黑格尔研究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即已开始进行。贺麟早在“西南联大”时期,就积极促成了中国哲学会“西洋名著编译委员会”的成立,准备有系统、有计划地引进西方哲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组成员中的贺麟、杨一之、王玖兴的专业方向都是德国哲学,老一辈学者因成长于旧社会,思想尚需改造,但他们又有海外留学经历,外语能力强,因此组织要求他们以文献和学术资料整理工作为主;而新中国培养起来的年轻学者的任务是从事研究和写作工作。特殊时代的特殊需求使得这项计划暂时缩小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的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第一部被翻译的黑格尔著作是《小逻辑》,即1817年出版的黑格尔《哲学科学百科全书》中第一部分“逻辑学”。贺麟自1941年为配合教学即开始着手翻译此书,1950年出版,1973年出版修订版。这本书在西方哲学类著作中发行量较大,它确立了黑格尔哲学基本概念的汉语译名,如“概念”“共相”“知性”“自在”“存在”“变易”“定在”“尺度”“实存”“反思”“理念”;而“有无”“对立”“统一”“差异”“扬弃”等概念,早已成为对现代中国人的哲学启蒙,有机地融入了现代中国哲学的系统当中。
1956年,贺麟启动并主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翻译。这是黑格尔用自己的观点对哲学史资料进行梳理的作品,是哲学家书写的哲学史的经典之作。该书时间跨度大,所涉及的哲学流派和人物繁多。贺麟与王太庆合作,该书第一卷于1956年出版,至1978年全部四卷的翻译和出版完成,每卷均附有术语或专名索引,为读者阅读和研究提供了线索。
1962年,贺麟与王玖兴合作翻译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出版,下卷的出版则到了1979年。该书被视为是黑格尔逻辑学和整个哲学体系的导言,其问题和理路有助于整体理解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脉络。为了对这部艰涩难解的作品进行导读,贺麟撰写了2万多字的导言与上卷同时出版,浓缩了他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心得。
杨一之1961年开始翻译黑格尔的《逻辑学》,1966年出版上卷,下卷的翻译完成于“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当中,1976年出版完毕。《逻辑学》是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全书共分“有论”“本质论”“概念论”三篇,内容广博、艰涩,歧义词较多。杨一之采用直译法,但对重要概念则做有学术见地的处理。例如Sein,一般译为“存在”,但杨一之根据黑格尔逻辑学的内容将之译为“有”,影响了学界对西方存在论的理解和研究。
在黑格尔哲学研究方面,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前,主要围绕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继承的关系而展开。1956年,张世英的《黑格尔的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至1972年第三版时,该书印数已超过20万册。这本以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思想为立场的小书成为当时青年人了解黑格尔思想的门径。1961年,由姜丕之与汝信合作、汝信执笔的《黑格尔范畴论批判》(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出版,这本书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对黑格尔逻辑学进行了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一书由王树人、叶秀山、余丽嫦、李凤鸣、汝信、侯鸿勋、薛华编著,汝信主编。该书虽然于1978年由人民出版社首版,但其主体工作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完成的。
改革开放初期,对黑格尔哲学自身的研究终于可以登堂入室,当时的黑格尔研究中心仍然在以贺麟为中心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汝信较早关注对黑格尔早期著作的研究,他于1978年发表了两篇论文,一篇是5万多字的《青年黑格尔的社会政治思想》(《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第1辑,1978年),另一篇为《青年黑格尔关于劳动和异化的思想——关于异化问题的探索之一》(《哲学研究》1978年第8期),两篇论文提供了当时不为学界所熟知的黑格尔作品的材料,而且在探究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问题上有所突破。1988年,贺麟翻译出版了《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商务印书馆),为了解黑格尔实践哲学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1989年宋祖良出版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青年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湖南教育出版社),梳理了黑格尔在写作《精神现象学》之前的思想。
这段黑格尔哲学的研究热潮中,对黑格尔哲学自身的关注和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展。薛华首先翻译出版了《黑格尔政治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为黑格尔研究领域的拓展提供了文本支持。薛华1983年出版的小书《自由意识的发展》,对《精神现象学》中有关自由的学说进行了阐述和探索性思考,这个方向在当时颇为新颖。这本书是在洪堡基金的资助下在“黑格尔档案馆”完成的,选题和写作过程中都曾与奥托·珀格勒尔(Otto Pöggeler)讨论过,是改革开放初期国际学术交往的较早体现。1986年,薛华又出版题为“黑格尔与艺术难题”的小薄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该书将现代哲学的视角融入,追问了黑格尔艺术终结命题对20世纪诸家如弗洛伊德、胡塞尔、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阿多诺等的思想的影响,是一部围绕问题展开研究的著作,至今仍有思想价值。
1982年,侯鸿勋著《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王树人著《思辨哲学新探》(人民出版社)出版,该著从黑格尔原著出发,批判性地探讨了黑格尔哲学体系和其中的具体概念如历史主义、整体观的合理内涵和价值,打破了国内长期以来从马列经典论述出发诠释黑格尔哲学的思想禁锢,为黑格尔哲学研究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该书一经出版即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后多次重印、再版。
1986年,贺麟著《黑格尔哲学讲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收集了贺麟对黑格尔整个哲学思想体系的研究论文及演讲共24篇,包括1930年的《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和1944年的《黑格尔理规学简述》两篇早期著作。这些论文涵盖了贺麟对黑格尔思想背景、哲学体系全貌、黑格尔早期著作的研究,不仅意味着黑格尔研究步入正轨,而且也重新开启了中西哲学比较和对话的研究方向。
1988年,王树人著《历史的哲学反思——关于 〈精神现象学〉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系统探讨了“主奴关系”、恐惧与劳动等问题。
1997年,张慎的《黑格尔传》(河北人民出版社),结合黑格尔思想产生的文化背景,揭示了黑格尔著作的产生过程和思想发展脉络,为全面理解黑格尔哲学提供了一把钥匙。
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在黑格尔研究方面的领军作用外,张世英在黑格尔逻辑学研究方面,注入了对历史文献和文本的分析,这主要体现在他的《论黑格尔的逻辑学》(首版1959年,二版1964年,修订版1981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0年中最系统地研究黑格尔逻辑学的著作)和《黑格尔 〈小逻辑〉绎注》(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当中。他还主编了《黑格尔辞典》(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这是一部研究黑格尔的重要资料。张世英还把研究重心从黑格尔逻辑学转向了精神哲学,出版了《论黑格尔精神哲学》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强调哲学的中心课题是“人”,并且用“自由”来概括黑格尔精神哲学的本质。这个思想倾向与80年代思想解放的浪潮中对人的重视是分不开的。
邓晓芒的《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1992年出版(湖南教育出版社),突破了长期以来只讲求辩证法的合理内核的局限性,将研究的视角扩展到辩证法的语源学和生存论起源。1996年赵林的《黑格尔的宗教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和2004年高全喜的《论相互承认的法权—— 〈精神现象学〉研究两篇》(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出版,使国内黑格尔研究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对宗教哲学和法权哲学、承认理论的重视,表明学界开始意识到黑格尔实践哲学的价值。
进入21世纪以来,梁志学2002年翻译出版黑格尔《逻辑学——哲学全书第一部分》,该书是继贺麟黑格尔《小逻辑》经典译本之后的优秀译本。作为研究性译著,书中有180余条译者注,提升了译本的知识性和专业性。2005年,梁志学建立了“历史考订版”《黑格尔全集》翻译课题组,这套书的蓝本为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科学院版《黑格尔全集》,目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5卷,它们是:《黑格尔全集》,第6卷《耶拿体系草稿(I)》(郭大为、梁志学译,2015年),第7卷《讲演手稿II(1816—1831)》(沈真等译,2012年),第10卷《纽伦堡高级中学哲学教程与讲话(1808—1816)》(张东辉、卢晓辉译,2012年),第17卷《宗教哲学手稿》(梁志学、李理译,2011年),第27卷·第1分册《世界史哲学讲演录(1822—1823)》(刘立群、沈真、张东辉、姚燕译,2015年)。这项翻译计划仍在进行之中。
与此同时,张世英领导翻译二十卷本“理论著作版”《黑格尔著作集》,现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3卷《精神现象学》(先刚译,2013年),第10卷《精神哲学》(杨祖陶译,2015年),第16卷和第17卷《宗教哲学讲演录》(燕宏远、张国良译,2015年),第7卷《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2016年)以及第2卷《耶拿时期著作(1801—1817)》(朱更生译,2017年)。
二 康德研究
康德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对德国哲学乃至哲学本身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多种史料表明,康德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更早,影响更广泛,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都涉猎过康德哲学。1946年,郑昕出版了从新康德主义的观点来理解康德的专著《康德学术》(商务印书馆),贺麟认为“这可能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一本专论康德哲学的著作”。该书把康德的认识论视为康德哲学大厦的基石,同时指出康德的认识论的最终旨归是道德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至改革开放前,康德认识论却一直被当作唯心主义而遭到批判,那时关于康德哲学的论述都只是在康德思想梳理的基础上加上批判的帽子而已。1949年,郑昕发表了新中国第一篇关于康德哲学的论文《康德哲学批判》,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肯定了康德哲学中的合理成分,同时,批判康德哲学中“理性”与“物自体”的分裂,批判康德认识论忽视了社会实践的重要性。1957年,齐良骥发表了康德研究著作——《康德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及其形而上学思想方法批判》(人民出版社)。这本书准确叙述了康德哲学的思想背景和基本精神,但囿于那个特殊年代的要求,该书不得不对康德哲学进行了带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批判。
对康德哲学的真正热情伴随着“科学的春天”的到来。1979年,李泽厚推出《批判哲学的批判》(人民出版社)一书,唤醒了人们对康德哲学的重新审视和高度热情。这本书具有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作品的全部特点,其学术性在今天看来或许有较多问题,但书中对康德哲学的“主体性原则”的意义的阐发却激发了整个知识界的兴趣,其原因与“文化大革命”惨剧对人性的泯灭后对人的重新发现和关注密切相关。从此,哲学界对康德的热情一发不可收拾,不仅在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领域内部出现了先黑格尔、后康德的现象,后来甚至提出了“宁要康德不要黑格尔”的极端口号。1981年,值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版200周年和黑格尔逝世150周年之际,“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办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到了时任国际黑格尔协会主席一职的柏耶尔(Bayer)教授、国际康德学会主席冯克(Funk)教授和国际黑格尔联合会主席亨利希(Henrich)教授出席会议并作学术报告。这次会议之后,以哲学所的名义编辑出版了纪念文集《论康德黑格尔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17篇论文中,康德研究占7篇,包括李泽厚的《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叶秀山的《康德的先验宇宙论的二律背反》、陈元晖的《康德的时空观批判导论》、郑湧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新形而上学导论——康德的 〈纯粹理性批判〉》等,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哲学界研究康德哲学的新起点,尽管该文集“编者的话”称此书的目的仍是“批判地继承他们的丰富的思想遗产”,因为“我们感兴趣的应该是从康德、黑格尔继续向前的运动,从唯心辩证法到唯物辩证法的前进运动,而决不能回到康德去,回到黑格尔去”。2004年学术界迎来了杨祖陶和邓晓芒集7年劳作之力推出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的最新中文译本(人民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李秋零花费十年心血,推出了9卷本《康德著作全集》,“全集”以普鲁士王家科学院本为蓝本。2018年,商务印书馆推出了王玖兴主译的《纯粹理性批判》,该书虽因王玖兴于2003年去世而未能全部完成,但王玖兴在德国哲学研究和翻译上的精深造诣,使得这部译著一经出版即受到学界的推崇,它为西方哲学的汉语转化树立了一个新标杆。这些译本不仅为更多的人阅读康德提供了可能,而且也代表着中国学者对康德哲学的理解和诠释。
与黑格尔研究相比,康德研究之前的不受重视似乎也给改革开放后的康德研究带来新的契机。当人们抛弃了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批判之后,康德研究从一开始就比较关注在文本解读基础上讨论康德哲学当中的基本问题,首先是认识论问题。较早的专题研究成果有1990年韩水法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康德物自身学说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该书既重视了理论分析和文本考证,吸收了西方已有的康德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同时也注重批判性地考察康德之后西方哲学中“物自身”学说的问题线索。陈嘉明发表了《建构与范导——康德哲学的方法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把康德思想的方法论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张志伟《康德的道德世界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从整体性角度出发进行分析,指出康德批判形而上学的目的乃在于重建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是一种以自由为基础、以道德法则为形式、以至善为根本目的的“道德世界观”。这本书为深入理解康德哲学开辟了新途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现代西方哲学进入人们的视野,促使康德哲学研究有了更多的思想路径,康德哲学全面开花,进一步凸显了康德哲学作为重要思想资源的当代意义。黄裕生的专著《真理与自由——康德哲学的存在论阐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较早地直接提出摆脱把康德哲学当作认识论来理解的传统的主张。受海德格尔哲学影响,黄裕生尝试从存在论的角度出发,揭示出了康德哲学中真理与自由相统一的面向,明确了自由原则作为西方早期现代社会的根基的认识。
赵广明的《康德的信仰——康德的自由、自然与上帝理念批判》(凤凰出版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整体性地考察康德的批判哲学,指出在可能现场无人范围内知识是有效的,而在知识或经验之外则是信念、信仰的领域,道德或宗教的领域,后者之所以可能皆因自由的理念。这是较早关注康德宗教哲学的书。
叶秀山多年研读康德哲学的论文以“启蒙与自由”为题结集出版(凤凰出版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24篇论文中多篇为进入21世纪以来的新作,如《康德的法权哲学基础》和《试析康德“自然目的论”之意义》。叶秀山把康德置于整个欧洲哲学的发展史上,通过对理性僭越自身的、因而也是自由的“自然倾向”的讨论,牢固确立了“自由”概念在康德哲学中的地位。对于《判断力批判》,叶秀山不再拘泥于其审美著作的共识,认为它是沟通《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所涉及的两个独立领域的“桥梁”,《判断力批判》所涉及的正是人作为自由者的真实的“生活场所”,也就是胡塞尔、海德格尔提到的“生活”的“世界”,打通了德国哲学从古典到现代的一个发展环节。论文集还一反过去认为批判哲学的意义在于从传统的本体论向知识论的转向之上,提出经过批判的形而上学也能够成为一门具有“范导性”作用的“基础”“科学”,开启了重新考察“本体论—存在论”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地位的契机。
借助英美分析哲学视角研讨康德是近年来的热点。陈嘉明在《概念实在论:康德哲学的一种新解释》(《哲学研究》2014年第11期)一文中,从布兰顿提出的“概念实在论”出发,提出康德哲学是实在论的,因为它坚持承认对象的独立存在;同时康德哲学又是概念实在论的,因为康德的实在是经我们的概念构造后的结果。
与此同时,对康德政治哲学的现当代意义的重新开掘也吸引着很多康德研究者。康德并不只是个“纯粹”的书斋型学者,按德国当代哲学家赫费的说法,康德的理论哲学在历经200年后依然能够成为“现代哲学的基石”,其实践哲学中世界主义的法权哲学与和平理论在全球化的今天对世界保持强大的吸引力。康德的世界公民理论为当代全球化提供了一种理性而高端的哲学、政治学和法学理念。关于“永久和平”的思想也得到了讨论,如郭大为的论文《政治的至善——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与当代世界》(《云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郭大为提出,永久和平是贯穿整个康德哲学及其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主题。康德在政治—法哲学领域完成了一场哥白尼革命,用和平的国际法代替了战争的国际法,永久和平从而成为判断和衡量人类的道德进步和现世幸福的最高尺度,它是政治的至善,是康德政治—法哲学的拱心石。尽管康德的许多提法在今天需根据时代变化作出修正与拓展,但他所确立的原则与精神在今天仍显出其特有的理论生命力。
邓晓芒从康德道德哲学的视角出发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和“拯救”引人注目,尽管来自儒家学者圈的批评不断。邓晓芒指出,儒家伦理具有一种结构性的伪善。对此,康德通过现象和自在之物的区分构成了这种结构性“乡愿”的解毒剂,也就是我们应该从根本上摒弃“替天行道”的思想,在我们所敬重的道德律面前保持谦卑。儒家视道德为“治国安邦”的手段,一味地强调有德者得天下,但是却不去考虑“天下”—国家体制本身是否有道这一政治学当中应当考察的首要问题,这种政治功利主义立场进一步地把结构性的“乡愿”变成了体制性的“乡愿”。从康德的立场出发,这种把道德建立在经验性原则基础之上的做法摧毁了道德及其崇高性,而康德对此所开的“药方”是把道德的根基建立于不可知因而也不可限定的自由意志之上,使得人心兼有本性的恶和人格的自由独立。这种建立在自由意志基础之上的道德才是真正的道德,它能够在面临危机的时候进行自我修复和更新,从而避免全面的崩溃。康德对伪善的批评则是从人性和人格中生来就伴随着的自欺结构入手的。儒家的大部分道德范畴在康德那里都可以保留,但它们的根基应该变成理性和自由意志,而不是那种狭隘的自然情感如孝、悌。这样一来,儒家的道德观就不再是那种自我纯洁感和自恋,而是包含有彻底的反躬自省成分。儒家伦理在今天日益走入困境,特别是日益暴露出其乡愿的本色,其根本症结在于他们的人性观中缺乏自由意志的深层次根基,因此需要经过一番理性的加工和阐释,而这种加工在康德哲学里面可以找到更多的理论工具和资源。[※注]
三 费希特研究
汉语费希特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中心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1986年,王玖兴翻译出版了费希特的《全部知识学基础》一书(商务印书馆)。这本书是费希特哲学体系的基石,也是理解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思想演变的必读书,其内容之艰深、语言之晦涩对于德语母语的人来说也是共识。王玖兴的翻译越在晦涩难解之处,越见功夫,为学界有目共睹。
1988年,梁志学组建了《费希特著作选集》翻译课题组,确立了“翻译基础上研究,研究指导下翻译”的原则,在与国外同行不断交流的前提下,先后翻译出版了费希特的四部著作:《论人的使命学者的使命》(梁志学、沈真译,1984年),《伦理学体系》(梁志学、李理译,1995年),《现时代的根本特点》(梁志学、沈真译,1998年)、《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梁志学、沈真、李理译,2003年)。这些高质量译本为中国的费希特研究奠定了基础。尤其是《论人的使命学者的使命》一书因译笔精纯而多次印刷,它已成为有良知的纯粹知识分子的思想纲领。洪汉鼎翻译了费希特书信集《费希特:行动的呐喊》(1988年)。
梁志学领导和亲自参与的费希特翻译和研究工作填补了国内费希特研究的空白,并为其向纵深方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梁志学在翻译的基础上,先后完成了三本具有宏大叙事风格的著作的写作:《费希特青年时期的哲学创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费希特耶拿时期的思想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和《费希特柏林时期的体系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这三本书以费希特思想发展的时间线索为出发点,以翔实的材料准确而有序地展开了费希特思想的内在理路和发展历程,讨论范围几乎涵盖了费希特思想的全部范围。同时,程志民的《绝对主体的构建——费希特的哲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谢地坤的《费希特的宗教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郭大为的《费希特伦理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李文堂的《真理之光——费希特与海德格尔论SEIN》(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都是在以费希特为对象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成书的专著,对费希特宗教哲学和伦理学的系统研究在国内尚属首次,至此,费希特哲学研究初具规模。2004年,谢地坤、程志民还合作翻译了费希特《自然法权基础》(商务印书馆),这是费希特应用知识学原理对法学领域所做的研究,是德国古典哲学中对民主原则阐述最深刻、最全面的名著。
四 谢林研究
相比于康德、黑格尔研究,谢林研究一直相对薄弱。梁存秀、薛华于1973年春起翻译反映谢林青年时期的思想的著作《先验唯心论体系》,1975年冬完成,最终发表于1978年。梁存秀结合这本书的翻译,研读了谢林的重要代表作,写出长篇译者前言,向广大读者介绍了这位德国古典哲学家从拥护法国革命到充当封建专制辩护士的思想历程。
青年学者先刚近年来在谢林的翻译和研究方面作出了成绩。他主编的21卷本《谢林著作集》自2016年起由北京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现已出版的卷册有:《近代哲学史》(2016年),《哲学与宗教》(2017年),《世界时代》(2018年),《学术研究方法论》(2018年),《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2019年)。与著作集翻译同时进行的还有谢林哲学思想研究,先刚已出版专著两部,它们是:《永恒与时间——谢林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和《哲学与宗教的永恒同盟——谢林 〈哲学与宗教〉释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打开了谢林研究的格局。
邓安庆翻译出版了谢林的《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其相关对象的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和《布鲁诺对话——论事物的神性原理和本性原理》(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两部著作。
王建军关注谢林后期哲学思想,出版有专著《灵光中的本体论——谢林后期哲学思想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这个研究方向与国际学界是一致的,研究者注意到晚期谢林思想中的非理性因素对于从德国古典哲学向晚期现代哲学的转换环节的意义。
五 小结
德国哲学对中国学人的吸引力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从康有为、梁启超等清末学人对康德学说的介绍起,今天的中国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至少历经四代人,我们拥有一大批出色的德国哲学的研究者,人员组成涵盖了不同年龄段。在研究成果方面,三代学者的努力为我们打造了重要著作的经典译本,用汉语理解和阐释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框架也已搭建起来,很多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不比英语世界的成果逊色。难能可贵的是,从老一辈学者贺麟、张世英,经叶秀山、王树人一直到邓晓芒,他们将德国哲学作为思想资源,自觉地将之与中国哲学传统相结合,丰富了我们对西方哲学的整体认识,更深化了我们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反思。相信在未来,世界范围内的德国哲学研究领域将听到更多的来自中国的声音。
显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