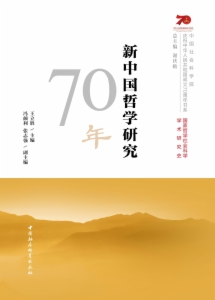第三节 70年来中国美学史研究状况
|
来 源
:
|
新中国哲学研究70年 \ - |
作 者
:
|
- |
浏览次数
:
|
6 | ||
|
摘 要
:
|
1949年以来70年的中国美学史研究,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段。除以上几种通史性著述,还有许多各具所见的著述,如林同华《中国美学史论集》 ( 1984年) ,栾勋《中国古代美学概论》 ( 1984年) ,皮朝纲《中国古典美学探索》 ( 1985年) 、 《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概要》 ( 1986年) ,曾祖荫《中国古代美学范畴》 ( 1986年) 。《中国美学通史》 ( 8卷)大体遵循了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的美学思想史写作观念— — “抓住每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美学思想家和美学著作” — —但是除了具体内容上的扩展,如宋明理学、心学的影响等,汉代卷身体美学、政治美学,宋代部分的“休闲文化与美学” 。其实,整个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也需要类似的文献研究作基础。 | ||||||
|
关键词
:
|
美学 美学史 美学思想 美学范畴 禅宗 宗白华 美学史研究 意境 境界 著作 通史 |
||||||
在线阅读
第三节 70年来中国美学史研究状况
字体:大中小
1949年以来70年的中国美学史研究,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段。1950—1966年为第一时段,是中国美学史研究和学科建设的起步期;1978—2000年为第二时段,是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收获期和全面发展期;2000—2019年为第三时段,是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反思和调整期。
一 起步期:1950—1966年
1949年之前,只有个别人自觉地进行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主要是邓以蛰和宗白华。群体性的,具有学科建设意义上的中国美学史研究,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促成这一发展的,主要有三个大环境方面的因素。第一,新文化建设中,继承优秀民族文化遗产的要求。1951年,周扬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发表题为“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演讲,引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中的话,重提继承优秀民族文学艺术的意义。在这样的氛围中,古代文艺理论的整理和研究顺利开展起来。第二,美学大讨论的影响。50年代开始的美学大讨论,引起了学术界对美学的普遍热情,于是一部分古代文艺理论的研究很方便地转化为古代美学的研究。其间褚斌杰于1956年7月在《文艺报》(1956年第14号)发表《重视中国古代美学著作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这种转化。第三,1961年的“中国美学史”教材建设。1961年,中宣部和高教部统一组织高校文科教材的编写,成立了各个编写组,“中国美学史”是其中之一,由宗白华负责。“中国美学史”编写组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美学史学科建设正式启动。
伴随着美学大讨论的展开,大约从1956年开始,中国美学的研究渐渐活跃起来,陆续有一些古代美学的专题论文发表。1956—1957年,邓以蛰发表《关于国画(一)》《关于国画(二)》《画法与书法的关系》,宗白华发表《美学的散步(一)“诗/文学和画的分界”》(1957年)、《中国艺术表现里的虚和实》(1961年)、《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1962年)、《中国古代的音乐寓言与音乐思想》(1962年),马采发表《顾恺之的艺术和他的“传神”美学》(1959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的《江海学刊》在1962—1963年发表了一些古典诗歌美学方面的论文,如佛雏《刘熙载的美学思想初探》(1962年),吴调公《论司空图的“诗”的美学观》(1962年)、《“别才”和“别趣”—— 〈沧浪诗话〉的创作论和鉴赏论》(1962年)[※注],吴奔星《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境界”论》(1963年)。
这时期有两个论争对中国古代美学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一个是始于1948年的关于国画改造问题的论争,既是改造,就有继承的问题,于是有如何理解国画特别是文人画的问题。这个论争一直延续到1957年,邓以蛰《关于国画》《画法与书法的关系》,就是对这一论争的回应。一个是关于境界/意境的论争。王国维《人间词话》里的“境界”说一直是人们热心谈论的话题,1957年李泽厚发表《意境杂谈》一文,引发了一连串关于意境或境界的讨论。李泽厚试图用“典型”论解读意境,他以主客观的统一解释“境”,以情理的统一解释“意”。李泽厚的文章本是理论的探讨,而激起的关于意境或境界的讨论却走向了历史的方向,即从对王国维的境界说的分析,走向对诗论史上起于唐代的意境或境界理论的探究,甚至再往前追溯到六朝时期的意象理论,形成了所谓意境或境界的概念史研究。还有人更进一步,把意境或境界视为中国诗歌美学的核心概念,而整个诗歌美学史就成了意境或境界概念的生成发展史(这直接导致了80年代和90年代诸多以意境或境界为中心的中国美学史建构)。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美学史研究中心,无疑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其时北大哲学系,中国美学方面有邓以蛰、宗白华、马采三位巨擘,他们是中国美学史建设的开拓者和推动者。1956年北大哲学系成立了美学小组,曾油印邓以蛰1949年之前的《书法之欣赏》《画理探微》《六法通诠》《辛巳病馀录》等著作作为研习材料。其后则有两次课程对中国美学史研究发生过较大的影响。一是1958年马采在北大哲学系讲授的中国美学课程,共八讲,以时间为序,但所述止于六朝[※注]。这个课程是在邓以蛰指导下进行的,对于唐代以前的美学,纲要初具,尤其第一讲从“羊”“文”“音”三个字切入,研究我国古代审美意识的发展,极具启发。另一个课程是1962—1963年宗白华为北大哲学系(1962年)、中文系(1963年)开设的中国美学史专题课。此课程共计五题,涉及先秦工艺美术,古代哲学、文学、绘画、音乐、园林建筑中所表现的美学思想,内容极丰富,规模很宏阔,尤其是对《易经》中所含美学思想的分析,具有开拓的意义。至于善从各种艺术中探究中国美学思想,更是宗白华的所长。除了这个讲座记录,此时期宗白华还留下了大量研究札记,如《古代画论大意》《建筑美学札记》《中国美学思想专题研究笔记》等,从这些笔记来看,他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从多个方面着手进行中国美学史的建设,作了许多精心的准备。可惜这项工作不久就被“文革”打断了。不过此时期在中国美学史资料的收集方面,却另有一个重要的成果,即北大哲学系美学教研室完成的《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这项工作1961年启动,在“文革”开始前的1963年完成,所选从《左传》开始,直到清末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的相关论述,历代美学思想的精华大略都在此了。这项重要的工作成果,在“文革”期间被束之高阁,但是为“文革”后美学研究的迅速兴起提供了最基本的资料支持。
二 全面展开期:1978—2000年
(一)收获期与第一个高峰:1978—1990年
“文革”十年,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处于停滞状态。但是“文革”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和教学迅速恢复,并很快进入了收获期。1983年,《复旦学报》编辑部编辑了一部《中国古代美学史研究》专辑,选录了1980—1982年两年间发表在各地学报上的中国美学史论文30篇,其中人物专论23篇,从老子到蒲松龄,覆盖面很广,可见风气之盛。这些专论为美学断代史和通史的撰写提供了基础。
80年代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中心有两个,一个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文学所。在介绍这两个美学中心的研究情况之前,我们先略述其他方面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成就。首先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施东昌(1931—1983年)的《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述评》(1979年)、《汉代美学思想述评》(1981年),前书评述了孔子、墨子、老庄、孟子、荀子、韩非的美学思想,后书评述了董仲舒、《淮南子》、扬雄、《白虎通义》及班固、王充的美学思想。作者的意图有两个,一是“努力去打开中国美学遗产的宝库”,这是书中“述”的部分;二是“揭示中国自古以来美学思想斗争的历史发展规律”(《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述评·序》),这是书中“评”的部分。两书“述”的部分,较为充分地呈现了先秦两汉时期人民对于美学问题的各种见解,这是两部著作的价值所在;“评”的部分,“努力揭示各个作家和著作的美学思想究竟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是朴素辩证法的还是形而上学的……从而给以适当的肯定和否定的历史评价”(《汉代美学思想述评·序》),这是历史的痕迹,毫无意义。郭因(1926—)《中国绘画美学史稿》(1981年)也有浓厚的历史痕迹。据作者的序,该书意旨是尝试从美学的角度来研究与撰写中国绘画理论的发展史,并用以阐扬毛泽东主席的文艺思想,即“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美学思想和创作方法。该书探讨了从先秦至清代历史上重要的绘画美学家的美学思想,并一一说明他们是现实主义者还是浪漫主义者,是何种类型的现实主义者或浪漫主义者。对于每一时代,又有专章小结此时代绘画美学思想斗争与发展的情况,分析此时代绘画美学思想斗争与发展的历史背景。因为作者本是画家,所以其在具体分析上每有洞见,如他认为同样主张写实的,又有重形似与重传神的不同。刘纲纪《书法美学简论》(1979年)也带有历史的痕迹,即坚持在“现实主义”的原则下,讨论书法美的来源,斥重视书法之抽象美的观点为唯心主义。在具体的论述中,他遵循邓以蛰《书法之欣赏》中的思路,把书法的美区分为形态美和意境美,但是进一步把书法的形态美分为具有建筑性的静态美(篆书、真书)和具有音乐性的动态美(行草书)。
北大的美学研究因为“文革”前的丰厚积累,“文革”后迅速恢复并发展起来。1979年,宗白华“文革”前的“中国美学史专题”讲课稿(叶朗整理)以“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为题发表,奠定了80年代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基本框架;1980年初,“文革”前完成的《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终于由中华书局分上、下册出版;1981年,宗白华的《美学散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三部著作的发表,代表了中国美学史研究在新时期重新起步,也为新时期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树立了典范——富有时代气息的较纯粹的中国美学史研究。“文革”后,年青一代的于民、葛路、叶朗承担起了北大的中国美学史和中国美学专题的教学、研究任务,他们不同程度地继承了邓以蛰、宗白华中国美学史研究的那种纯粹性质,并很快作出了成绩。1982年,葛路《中国古代绘画理论发展史》、叶朗《中国小说美学》先后出版。《中国古代绘画理论发展史》是第一部完整的画论史著作,作者的意图在“恢复绘画理论的历史真面目,拂去一切误解的尘埃”(新版跋语),故其叙述简洁明了,分析尤有分寸,不做过度的发挥。叶朗《中国小说美学》也是该领域的开创之作,此书“清理出了一条中国古典小说美学和近代小说美学的发展线索,揭示出了中国小说美学史的概貌,初勾勒出了中国小说美学体系的大致轮廓”(郭瑞)。1984年,于民《春秋前审美观念的发展》出版。此书依据出土材料(陶器、玉器、青铜器、甲骨文)和早期文献,将春秋前(包括春秋时期)审美观念的发展理出了个初步轮廓,并重点讨论了春秋时期美与善、文与质、乐与悲等7对审美范畴的出现和影响。正如作者所说,这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先秦诸子的美学思想有重要的意义。上面的三种著作,都是著者在所开专题课的基础上写成的,在各自的领域也都有开创之功,而且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当然,代表着80年代北大中国美学史研究最高水平的是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1985年)。这是第一部较完整的中国美学史(始于“老子的美学”,讫于“李大钊的美学”),材料翔实,分析细致,而叙述简明清晰,在宏观的把握和细节的处理上都很出色。此书大致以人物和著作为纲,而又紧扣审美范畴和审美命题这个中心;作者把任务限定在“把历史上每个时期美学思想的本身面貌以及美学思想的前后发展线索搞清楚”,所以极少枝蔓(指社会背景方面)。在中国美学史的认识上,作者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看法。其一,提出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分期问题,以先秦两汉为古典美学的发端,魏晋至明代为古典美学的展开期,明末与清为古典美学总结期。其二,明确指出在中国古典美学体系的中心范畴不是“美”,而是“审美意象”。其三,区分了审美意识的形象系列和范畴系列,认为美学史应该研究表现为理论形态的审美范畴系列,而不应该是形象系列。作为一部“大纲”,遗漏在所难免——如著者自己所说,禅宗和理学维度的缺失是最大的不足——具体的观点可议之处也不少,但是都不妨碍它成为中国美学史研究上的最好的典范之一。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室甫一成立,李泽厚即提议组织室里的力量,编写一部完整的中国美学史。作为铺垫,李泽厚整理自己的札记写成《美的历程》(1981年),为计划中的《中国美学史》粗略勾画了一个整体轮廓。《美的历程》包括十个部分,对中国文化中的审美意识、审美风潮作了一次鸟瞰式的历史巡视,从原始图腾到明清文艺思潮共十章,其中先秦理性精神(三)、楚汉浪漫主义(四)颇能道前人所未道。此书攫取了各个时代审美风尚的主要精神、审美意识流变的节点,体现出一个思想家的宏观视野和对各个时代精神的精准把握。从广义的美学史来说,这是第一部中国美学通史——以审美意识的形象系列呈现出来的中国美学史。但它当然不仅是审美“形象系列”的呈现,更有价值的是其对审美意识背后文化精神的分析,它的魅力也在于其思想的穿透力。
《中国美学史》的第一卷“先秦两汉”、第二卷“魏晋南北朝”先后于1984年、1987年出版。与《美的历程》不同,《中国美学史》取审美意识的范畴系列为论述角度。但是与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不同,《中国美学史》更重视审美意识的思想史、哲学史背景,在分析美学范畴时,更侧重其中的哲学意义。这使得它对于中国美学的特质、中国美学的分期都染上了浓厚的思想史、哲学史色彩。它结合着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去观察中国美学的基本特征,总结出中国美学的六个特点:第一,强调美与善的统一;第二,强调情与理的统一;第三,强调认知与直觉的统一;第四,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第五,富于古代人道主义的精神;第六,以审美境界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在分期方面,先秦两汉之后,它把魏晋至唐中叶划为一期,晚唐至明中叶为一期(禅宗影响),明中叶到戊戌变法前为一期(心学影响)。它的构架是唯物发展史观和儒、道、骚、禅四种思潮之变奏的双重结构,这使得它的美学史叙述带有很强的构造性和哲学意味,阶级分析的痕迹也还不少。在具体内容方面,它的全面与分析的细密是前所未有的,可惜这个工程中止于第二卷的出版。1988年,李泽厚著《华夏美学》,完成了他儒、道、骚、禅之交织变奏而统摄于儒的中国美学叙述。据其前言,此书的目的是要说明华夏美学在魏晋时如何以儒为主体而吸收、包容了庄、骚,在唐宋又如何接纳禅宗而发展出宋明理学“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审美境界——这是汲取了庄、骚、禅之后华夏美学的最高峰。
《中国美学史》第二卷出版的1987年7月,敏泽的《中国美学思想史》第一卷(史前时期至南北朝)出版,第二卷(唐至明清)、第三卷(近代和现代)于1989年出版。敏泽的《中国美学思想史》代表了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新水平,它的出版,也可算是80年代中国美学史研究的一个完美结局。其特色有三点:第一,思想史与美学史的结合。全书按时代顺序分成若干编,每编前有一篇较长的绪论,叙其时代文化背景与审美意识的发展变化。第二,融合了审美意识的形象系列和范畴系列。他将原始记录和理论概括研究结合起来,将审美意识的活动形态和审美观念的理论形态的研究结合起来,对表现在各个历史时代的社会风尚、文化、哲学、宗教、艺术中的审美意识作通盘的考察,分析其中所包含的美学观念的实质和特点,辨析它们的生成和演化(皮朝纲评语)。第三,旁搜远绍,建立了美学思想发展历程中更为细致的人物坐标,对于一些美学研究中很少关注的人物如魏晋时的刘昼,或故意忽略的如清末的林纾亦予论列,以尽可能地呈现历史的细节。
80年代的中国美学史研究热闹非凡。除以上几种通史性著述,还有许多各具所见的著述,如林同华《中国美学史论集》(1984年),栾勋《中国古代美学概论》(1984年),皮朝纲《中国古典美学探索》(1985年)、《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概要》(1986年),曾祖荫《中国古代美学范畴》(1986年),葛路《中国绘画美学范畴体系》(1989年)[※注]等。其中林同华《中国美学史论集》选择若干重要历史阶段,考察当时各门艺术在创作与欣赏方面的审美原则,并对某些有代表性的美学思想家及其主要论点予以分析和评价(伍蠡甫序言),是一部由专论构成的断点式的中国美学史,他的研究深度和弥缝史、论的能力也都是一般人所不及的。皮朝纲《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概要》上篇范畴、下篇命题,颇有独到之见,如柳宗元“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的命题即经他的发覆而广为人知。曾祖荫《中国古代美学范畴》提出“情理”“形神”“虚实”“言意”“意境”“体性”六个基本范畴,首论其发展,次论其美学特征。此外,周来祥《论中国古典美学》(1987年)认为中国古代美学是“以和谐为美”的古典主义美学,于民《气化谐和——中国古典审美意识的独特发展》(1990年)认为,中国古典审美意识以气化论以及与它结合在一起的谐和论作为核心与根本,并以此贯穿其发展过程的始终(钟若)。80年代后期,开始有专题研究成果出现,如肖驰《中国诗歌美学》(1986年)、蒋孔阳《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1986年)、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论》(1988年)、金学智《中国园林美学》(1989年)、袁济喜《六朝美学》(1989年)。近代中国美学人物专题研究则有聂振斌《蔡元培及其美学思想》(1984年)、《王国维美学思想述评》(1986年)、林同华《宗白华美学思想研究》(1987年)、阎国忠《朱光潜美学思想研究》(1987年)。
审美范畴在80年代的中国美学史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事实上,除了《美的历程》,其他几部美学通史都是围绕审美范畴展开的。专门的中国美学范畴研究,始于80年代中期。大略与曾祖荫的《中国古代美学范畴》(1986年)同时,李欣复也在尝试对古代美学的范畴作系统的考察,他的长文《中国美学范畴史述略》(1985年)[※注]勾勒了古典美学范畴从先秦到晚清的生成、演进过程,把中国古典美学范畴描画成一个生展的有机体系——滥觞于先秦两汉,纯化发展于魏晋隋唐,深化总结于宋元明清。至80年代末,则有蔡锺翔发起并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研究丛书”。此丛书自80年代末陆续出版,从袁济喜《和——中国古典审美理想》(1989年)到曹顺庆、王南《雄浑与沉郁》(2009年),共出版了十余种范畴专题研究著作。此外,潘显一《大美不言——道教美学思想范畴论》(1998年)可算是一个新领域的开拓。
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仍有较多意识形态的痕迹——李泽厚在《中国美学史》第一卷的后记中犹批评此书有“对古人批判不够,肯定过多”“阶级分析较少,强调继承略多”的缺点。幸运的是,迅速而起的思想解放思潮让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很快就走出了意识形态的影响,80年代后期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不再强调“批判”,而是探迹钩沉,现其面目,发其幽光。
(二)全面展开与新思潮影响下的90年代
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全面展开,并走向细化,断代美学史、部门美学、人物专题、范畴专题,乃至一部经典著作(如《文心雕龙》《沧浪诗话》)的美学思想专题研究迅速发展起来。这时期,有延续80年代研究思路的,也有另辟新径的。另辟新径者,大抵与90年代的两个思潮有关,即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的“生命美学”思潮和“审美文化”思潮。
【断代美学史研究】90年代出版的第一部中国美学断代史是杨安伦、程俊的《先秦美学思想史略》(1992年)。此书依次讨论了中国原始期审美意识的起源和变化、甲骨金文和青铜器所见之审美意识、春秋战国时期的美学思想(包括诸子和《易》、屈赋中的美学思想),叙述较前人详备。此后则有吴功正的三部断代美学史《六朝美学史》(1994年)、《唐朝美学史》(1999年)、《宋朝美学史》(2007年)。吴功正的美学史研究已经有了较为广阔的“审美文化”视野,比如他的《六朝美学史》从六朝美学的历史动因、史的图式(审美范畴)、史的现象(门类美学)多个方面对六朝美学作立体的呈现。在历史动因方面,除一般人所注意的哲学动因(玄学、佛学)之外,还有庄园经济、社会风俗习惯方面的;门类美学部分,除一般人所注意的诗、书、画之外,还考察了乐舞、雕刻、园林及文学中骈、赋、散文、小说。审美范畴部分提出“丽”,从社会风习中的奢华之气、民俗风尚、士庶之分引出金粉美学、通俗美学、贵族美学,都有突破藩篱、开辟新境之功。此时期的断代美学史研究成果,还有霍然的《唐代美学思潮》(1990年)、《宋代美学思潮》(1997年)。霍然的断代美学思潮研究也有审美文化观念的影响。
【部门美学】90年代以后部门美学的成果很多,如庄严、章铸《中国诗歌美学史》(1994年),金学智《中国书法美学》(1994年)、尹旭《中国书法美学简史》(2001年),陈传席《中国绘画美学史》(2000年)。尤有意味的是周易美学、理学美学、佛教(包括禅宗)美学方面的开拓。周易美学方面,主要有王振复《大易之美—— 〈周易〉的美学智慧》(1991年)和刘纲纪《〈周易〉美学》(1992年)。后者是《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中相关内容的展开,前者则有较多新意——尤其是从“时”“生”“气”等多个方面突出了《周易》重生机流动之美的生命美学思想。我们知道,“生命”曾是宗白华阐释中国传统艺术时提醒出的一个重要概念。90年代的《周易》美学研究,又一次把“生命”的观念引入中国美学的研究[※注]。宋明理学美学方面,则有朱良志《扁舟一叶——理学与中国画学研究》(1999年)和潘立勇《朱子理学美学》(1999年),弥补了中国美学史研究中宋明理学维度的长期缺失。相比之下,佛教美学的研究更热闹些。最早提出佛教美学问题的是严北溟,严的《论佛教的美学思想》(1981年)从蒙昧主义、信仰主义和禁欲主义三个方面论证了佛教教义如何从反面,从不同的角度推动了佛教艺术的发展,并构成了佛教美学思想的基本内容。此后讨论佛教美学的论文陆续出现,如张文勋《儒、道、佛美学思想之比较》(1987年),蒋述卓《试论佛教美学思想》(1990年)。进入90年代后,佛教美学的研究渐多,先后出现了三部著作:王海林《佛教美学》(1992年)、祁志祥《佛教美学》(1997年)[※注]、《中国佛教美学史》(2010年)。在中国佛教美学研究中,最活跃的是禅宗美学研究,专著有皮朝纲《静默的美学》(1991年)、《禅宗美学史稿》(1994年)、张节末《禅宗美学》(1999年)。对其他宗派如天台、华严、净土等宗的美学思想的研究,则尚未起步[※注]。
90年代仍有一些全貌式或通史类的中国美学研究成果。韩林德《境生象外——华夏审美与艺术特征考察》(1995年)是一部“有心得,有新见”的著作(李泽厚评语)。作者受宗白华、李泽厚的影响较大,但他于发挥之外,补充、修正也很多,他的新见最突出的有两点:第一,认为“意境”乃是华夏美学的核心范畴和基本范畴。第二,以《周易》、元气论、阴阳五行说为“支撑华夏美学殿堂的三块思想史基石”,指出这三大思维传统产生于诸子学说之前,而其影响贯穿于整个华夏文明史。尤其是阴阳五行说对华夏美学的影响,作者论述最详尽,并从中得出“音乐性(时间性)是华夏艺术的灵魂”的结论。
陈望衡的《中国古典美学史》(1998年)是90年代唯一一部中国美学通史。此书充分吸纳了90年代中国美学范畴和部门美学研究的成果,规模庞大,体例亦较复杂,主要以人物为序,但时时杂以各种专题。它有个很长的“代序”,提出了华夏审美意识的四个基因,即“美真同体”“美善同义”“和合为美”“礼乐相亲”;一个绪论,提出了一个中国古典美学体系,即“以意象为基本范畴的美学本体论系统”“以味为主要范畴的审美感受论系统”“以妙为中心的审美品评论系统”,以及“真善美相统一的艺术创作论系统”。其书其说皆颇独特,可算是中国传统美学研究中的一道奇特风景。
三 反思和调整期:2000—2019年
进入21世纪,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景象颇为复杂,甚至有点光怪陆离的感觉。概括起来,大致有四个方面:第一,在新的哲学观念、美学观念和美学思潮影响下,新的研究范式层出不穷。第二,出现了对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中国美学史叙述范式的普遍反思。第三,围绕范畴、人物、经典著作展开的旧范式下的古代美学研究,“面”的扩大和“点”的细化、深化仍在继续。第四,充分发酵的国学热,为传统美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动力。项目基金支持催生了众多的大型研究工程,同时也让研究演变成了生产,出现了许多团体合作而成的“通史”“汇编”。
2000年,张法出版了自己的《中国美学史》[※注],在序言中,张法提出“重写美学史”的口号。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几种中国美学史叙述方式,都是以一种历史一元论演进的观点来写的,(而这个历史一元论演进模式,是西方中心主义学术范式下的历史一元论),忽略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独特趣旨。他要在轴心时代和分散世界史的新历史观下,呈示中国古代文化的独特趣旨、中国审美的独特风貌、中国审美的独特把握方式和理论形态,以便让“中国古代艺术的美学统一性……完全按照历史自身的方式呈现”。他的《中国美学史》确有不少独特之处:他突出了“文化”的意义,提出了自己的中国文化分期,并在此结构下“不按朝代人物论著一一排列,而着重说明中国美学史的整体逻辑,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各个历史时期的审美趣味核心”。具体内容上,他在艺术的各个领域及其专门理论、哲学之外,加入了另一个中国美学史的基因,即生活审美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娱);在士人美学、市民美学概念之外,增加了“朝廷美学”“民间美学”的两个概念;在轴心文化观念下,认为中国美学的独特性质形成于春秋时期,此后的时期,是此特性的展开与丰富,以迄于清——这一点上,与韩林德的《境生象外——华夏审美与艺术特征考察》(1995年)中的看法颇相近——然后他在分散世界史观下,把中国美学史的下限定在清末,此后中国的历史汇入了一元世界史,中国独特的审美方式到此为止,中国美学史也应到此为止。张法“重写中国美学史”的思考,表达了两个诉求:第一,中国美学史应呈现中国审美的独特性;第二,中国美学史应呈现中国审美现象的丰富性。这两个方面的诉求,是新时期的普遍呼声。
张法《中国美学史》(2000年)拉开了反思的序幕,此后的十年,“中国美学史”几乎让位给了“中国审美文化史”——当然,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审美文化”形态的广义中国美学史叙述。这类著作盛行于21世纪的头十年,而且都是多卷本:陈炎主编《中国审美文化史》(4卷,2000年);许明主编《华夏审美风尚史》(11卷,2001年);吴中杰主编《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论》(3卷,2003年);周来祥主编《中华审美文化通史》(6卷,2008年)。中国审美文化之丰富性充分呈现,使得人们对80年代形成的以范畴、概念、命题为中心的中国美学史叙述产生了普遍的怀疑,而如何呈现中国古典美学的“本来面目”也就成为一个共同的时代话题。因为中国古代并无“美学”这一学科,选择什么范畴作为中国美学的核心概念,就会形成不同的中国美学史叙述。一个最著名的例子是“意境”或“境界”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意象”或“意境/境界”渐被视为中国美学的中心范畴,以至出现了许多专门研究“意象”或“意境/境界”的著作,分析其结构并建构其历史,甚至借此建构美学史,其中较著名者如汪裕雄著《意象探源》(1997年),薛富兴著《东方神韵——意境论》(2000年),古风著《意境探微》(2001年)。这种看法在21世纪也开始受到质疑,萧驰(肖驰)曾经是“意境”论的宣传者(著有《中国诗歌美学》,1986年),但是其于21世纪出版的著作《抒情传统与中国思想——王夫之诗学发微》(2003年)、《佛法与诗境》(2005年)开始反省,指出诗境说远不能概括中国古代诗学中的一些重要传统,罗钢则进而说以“意境”为中国美学的核心范畴,本就是一个“被发明的传统”、一个“学说的神话”[※注]。
另一个角度的反思则与存在主义哲学的引入有关。20世纪80年代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潮,引发了对中国传统美学所隐含的现代性的思考。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1995年)、《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1999年)使我们认识到中国传统美学是一种存在论美学,而不是认识论美学[※注],因此中国传统美学所表现出的现代性,恰是它区别于西方认识论美学的独特性。存在主义带来了对生命的另一种关注,从而带来了另一种生命美学的方向。朱良志在21世纪的中国古代美学研究,即是这转向的代表。朱良志是把“生命美学”的观念贯彻到中国美学史研究最彻底的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1995年),到21世纪的《曲院风荷——中国艺术论十讲》(2003年)、《生命清供——国画背后的世界》(2005年)、《中国美学十五讲》(2006年)、《真水无香》(2009年)、《南画十六观》(2013年),“生命”是一以贯之的关键词。他的全部工作,都在阐发中国传统艺术、中国传统美学中的生命精神。但是这中间有一个转变:《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的哲学基础,是柏格森、宗白华的“生机”生命哲学,也是基于《周易》的“生生”和元气论的生命哲学,但是自《曲院风荷——中国艺术论十讲》开始,其哲学基础逐渐转向以存在主义的“生命意识”为核心的生命哲学,也是《庄子》尤其是禅宗的生命智慧的生命哲学。相应地,他从中国传统艺术阐发出的生命精神,也从对生机的欣赏转向对生命意义的追问、生命的安顿、生命智慧的开悟。他强调中国艺术中对人工秩序的规避,对拙的追求,真性的开启,从“二”回到“一”的智慧,都是生存境域的敞开——从客体回到主体,从认识回到存在。
20世纪新进来的另一些美学思潮也在推动着中国美学史的研究突破旧的范式。身体美学被引入中国美学史研究,成果有刘成纪著《形而下的不朽——汉代身体美学考论》(2007年),方英敏著《修心而正形——先秦身体美学考论》(2017年);环境美学、生态美学被引入中国美学史研究,成果有刘成纪著《自然美的哲学基础》(2008年),程相占著《中国环境美学思想研究》(2009年)、卢政等著《中国古典美学的生态智慧研究》(2016年)。也有来自内部的反省和调整。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叶朗有鉴于编于60年代的《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的局限性,发起编撰《中国历代美学文库》的工程,将中国美学史的文献拓展到审美风尚和审美设计。经过150余位学者10余年的努力,19卷的《中国历代美学文库》终于在2003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叶朗随后又组织8卷本《中国美学通史》的撰写,并于2014年完成出版。《中国美学通史》(8卷)大体遵循了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的美学思想史写作观念——“抓住每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美学思想家和美学著作”——但是除了具体内容上的扩展,如宋明理学、心学的影响等,汉代卷身体美学、政治美学,宋代部分的“休闲文化与美学”,明代部分的“长物为美”,显然是新潮流的影响。朱志荣主编的8卷本《中国审美意识通史》(2017年)则试图在两种审美文化史和美学思想史之间寻求平衡——从各时代的审美文化中分析出一条审美意识发展变化的历史。张法仍在继续他“重写美学史”的思考,提出:“在中国美学史本有的整体框架中,加上与物质形态—制度文化—思想观念—语言概念铸成相关联的美感的建立和演化这样一个核心,就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去看中国美学史书写中的点和面……就会有一个新的、更为丰富、更接近于中国古代原貌的展现。”[※注]在此指导原则下,张法编了一套视野更为宏阔的中国美学史资料——七卷本《中国美学经典》(2017年),与前人所编相比,增加了传统天下观和制度美学的内容。
在反思和调整中国美学史叙述方式的同时,中国美学史上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在继续推进。老话题的新研究如朱志荣的《商代审美意识研究》(2002年)、《夏商周美学史》(2009年),王明居的《唐代美学》(2006年),刘方的《中国禅宗美学的思想发生与历史演进》(2010年),潘立勇的《一体万化——阳明心学的美学智慧》(2010年)。范畴史的研究方面,李欣复出版了自己较成熟、完整的《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史》(2003年),该书详细阐释了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发展史,概述了几十对重要美学范畴在不同时期的流派和个人那里不同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三年后,王振复推出了三卷本的《中国美学范畴研究》(2006年),分期与李欣复略同。新领域的集中成果有潘显一等著《道教美学思想史研究》(2010年),祁志祥著《中国佛教美学史》(2010年)。近十年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皮朝纲先生凭一己之力,穷三十载于斯的既专且精的禅宗美学及文献研究,在近十年内结出的丰硕果实:《丹青妙香叩禅心——禅宗画学著述研究》(2012年)、《墨海禅迹听新声:禅宗书学著述解读》(2012年)、《中国禅宗书画美学思想史纲》(2012年)、《游戏翰墨见本心——禅宗书画美学著述选释》(2013年)、《禅宗音乐美学著述研究》(2017年)。这种文献研究,“用最笨的工夫,做着最有开拓性的工作”,为将来禅宗美学研究的质的进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其实,整个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也需要类似的文献研究作基础。
显示更多